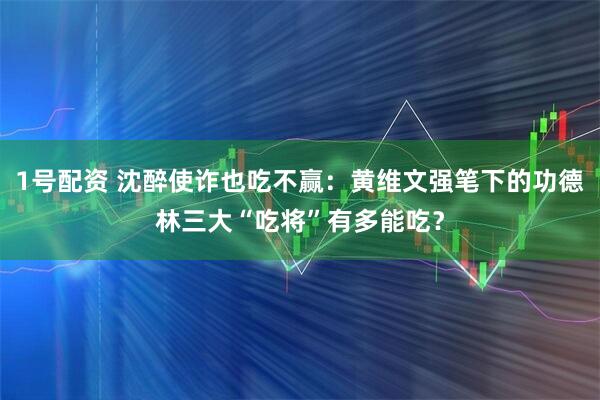
《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》的作者是原青年军第二〇六师少将师长邱行湘的外甥、第七十六军副军长黄剑夫之子黄济人——为了写好这本书1号配资,黄济人采访了大量特赦蒋军,就连一向不喜欢被打扰的黄维,也在被黄济人的诚意感动后提供了大量资讯。
我们可以把《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》看成报告文学,也可以将其视作进行了艺术加工的访谈录——那些颇具风趣幽默感的艺术加工,也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的,我们细看特赦将领黄维、文强、李以劻、沈醉等人的回忆录,也能跟黄济人的描述对上号,比如关于“功德林吃将”的描述,文强和黄维、沈醉都写了。

《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》评选出的三大“吃将”,一个能吃八块油饼,一个能吃十四个肉包子,一个用洗脸盆盛面条,现在可能很多人都不会理解:这些功德林“学员”文官都在厅长以上,武官都在少将以上(只有保密局浙江站站长章微寒是例外),被俘前锦衣玉食,食不厌精脍不厌细,怎么到了功德林忽然胃口大开,比搬砖的力工还能吃?
有这样的疑问,一点都不奇怪,因为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了,买肉都不愿意买肥的,饭碗也逐渐变小,在二十年前,吃饭吃面用的大海碗,几乎没有多少家庭会配备了。
黄济人在采访过程中为“吃将”的饭量震惊,黄维在《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》中却有些“幸福和感激的自豪”——他给老蒋卖命的时候落了一身病,在功德林治好后也是胃口大开:“粮食虽然也定量,每月四十五斤,但是亏空了另外可以报销,等于不定量。有些年轻的很能吃,我那时也很能吃,大馒头一顿要吃四个。”

原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一顿能吃四个大馒头1号配资,在功德林根本就排不上号,但是他大病初愈就能有如此饭量,也足以击败看这篇稿子的百分之九十九的读者了——笔者现在一两一个的馒头,每顿也只能吃一个,而四五十年前北方食堂的馒头,一个二两,而且是干面粉的重量,水是不算的。
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在北京,那是不折不扣的北方,北方的三两水饺、二两馒头,都是按干面粉计算,四个大馒头蒸出来总有一斤多。
据黄维回忆,当年功德林为了给他们治病,那可是费了相当大的力气的:治疗结核病的药物如链霉素和青霉素,我们国内自己还不能生产,都得靠苏联进口,可苏联的链霉素药物性能不好,而英、美两国的链霉素质量虽然过关,却又对我们封锁,于是公安部卫生机构只能专门派人到香港、澳门购买,就是这些高价格高质量的药品,救了黄维、杜聿明、康泽、文强、杜建时、范汉杰、徐远举等人的性命。
黄维在列出“病号”名单后还感叹:“这些人都有严重的结核病或其他严重的疾病,他们都和我一样,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。假如我仍旧在旧军队里,得了病就得离职回家。我黄某人的家底并不算厚,经济力量毕竟有限,即使典当一空,恐怕也未必能支付得起医治十年的那一笔数量可观的医疗费用。”

老蒋把部下往死里压榨,只要有一口气就得上战场,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杜聿明:当年杜聿明腰椎结核已经严重到坐不直,要在后腰上塞一个垫子才能撑住,但还是辽沈淮海两头跑,要不是在陈官庄被俘,在老蒋手下是绝对活不到七十七岁的。
功德林里走出了不少“长寿将军”,其中杨伯涛、郑庭笈九十一岁,文强、曾扩情九十四岁,文强在《口述自传》中感叹:“我家二十代以内都没有九十岁以上的人,我活到现在九十多岁,还在活。这是我很大的幸福嘛,我感觉非常圆满1号配资,感觉越活越有意义,我还有充沛的精力,不知老之将至。”
文强在《新生之路》中,承认自己很能吃,但跟其他同学相比,还是望尘莫及:“最著名的‘吃将’,一顿午餐能吃二两一个的馒头八九个;早餐油饼八张、三碗豆浆;晚饭十四个肉包子或十三个糖包子,吃面条用小脸盆盛,简直骇人听闻,我这个中等的,最大的量也不过五六个包子。”

文强没好意思点出那三位“吃将”的姓名,黄济人却没有那么多顾虑,因为其中有一个是他舅舅:“第四十七军中将军长严翌早餐可以吃八块油饼外加三碗豆浆;第九军中将军长黄淑午饭可以吃十三个糖包子或十四个肉包子;邱行湘晚饭则干脆用中号洗脸盆盛面条……于是除去老弱病残,这里的将军们谁不是心宽体胖、膀大腰粗?”
文强分析出了这些将军们如此“能吃”的主要原因:大家不再担心在战场上朝夕不保,而且炊事员尽心尽力,再加上学员们除了上课,还自己动手养猪养兔种菜种葡萄,适量的体力劳动增强了大家的食欲:“不论主食副食,花样总是变化无穷,无怪大肚汉们笑逐颜开了。”
我们在电视剧《特赦1959》中看到黄维和康泽都很不合群,以文强为历史原型的刘安国更是不停惹事,那还真不完全符合史实,起码文强就没有那么刁钻顽固,他还担任了功德林《新生园地》文艺专栏主编,沈醉、徐远举、黄维写诗,也得经他“审阅”,只不过文强的审核标准很宽松,表示“文责自负”,从不“毙稿”,看来当年的功德林《新生园地》,比现在很多平台人性化多了。

功德林里的将军们每天忙忙碌碌心情愉快,自然胃口大开,沈醉在《战犯改造所见闻》中的描述更为有趣:“由我分配菜饭时,李仙洲便提醒我,他是有名的大肚皮;我也不甘示弱回答他,我的饭量也不小。我分给他那一份菜土豆特别多,他那餐和我只吃个平手。我三碗,他也三碗。当时分菜,只要牛肉都是一样十来块,土豆多少就没有人去计较了,我特意多给他半勺土豆。”
沈醉“使诈”跟李仙洲吃成平手,等到吃面食的时候,沈醉就心服口服了:李仙洲这位王耀武都要叫一声“老大哥”的黄埔一期中将,二两的馒头能吃六七个,吃面条面片可以用小脸盆盛上半盆一气吃完,肉包子一次轻松愉快地吃下十一二个,超过沈醉四分之一,也就是说“年轻力壮”的沈醉一顿也“只能”吃七八个。
李仙洲赢了沈醉,却还排不进“吃将”前三名,这里我们还真有必要介绍一下他们的出生日期:李仙洲生于1894年6月17日,1947年在莱芜战役中被俘时已经五十三岁;沈醉生于1914年6月3日,1949年12月9日在昆明被捉时才三十五岁;杜聿明和黄维都是1904年的,王耀武比他们大两岁,文强比他们小三岁,这些人被俘时,也就是四十多点,现在还算中青年。

文强说功德林公认的这三大“吃将”饭量“简直骇人听闻”,可能是他还没有见过真正饭量大的,笔者在工厂上班的时候,动力车间主任一顿就曾吃过二十二个包子。
工厂食堂的包子是韭菜馅的,里面也没有多少油水,所以或许还不如功德林吃将的肉包子顶事,但销售科的力工们,却能一顿煮一斤干挂面,外加二斤猪头肉,装满满三大饭盒,用不上十分钟就全部吞掉,然后又去“装车皮”——一节火车车厢,九百或一千二百袋(每袋一百三十斤)豆粕,五六个人两小时装完,一袋一块钱,而我们当年的行政人员工资每月才四百块钱左右,他们挣得多,也吃得多,吃得好。
功德林“吃将”的饭量当然不能跟装卸工相比,而且还会让我们想起形容无用将军的四字成语——那个成语大家都能想到,笔者也学文强,就不明说了,最后只想问大家一个问题:在您见过或听过的大肚汉中,有多少能跟功德林“吃将”并驱争先?
红腾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